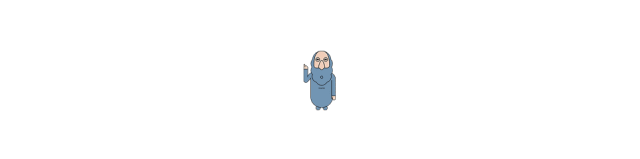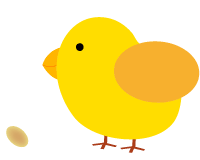按语:穆彭艳就人生意义的问题写了一篇札记,谌洪果回信答复。特将二人的交流分享给大家,希望有所启发。
穆彭艳:
以结果为视角看待人生的意义
你是否曾在一个难忘的时辰,在脑海中“过完”了自己的一生?
无论你是在何种年纪在脑海中预演一生的。“人生,必有一死”一定是这一思考的最初前提。假定,我们是从恰好的20岁开始“预想”整个人生——往前导,会有呱呱坠地的那一刻,会有懵懂的童年,阳光灿烂的少年,然后就是20岁左右。往后导是勇猛精进的青年,百转沉浮的中年以及世事沉淀的老年。
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玩耍、嬉戏、如饥似渴地学习,工作拼搏,恋爱结婚,生育子女……就这样在岁月流转中,不断长大,不断变老,直到生命停止在某一刻,化为一捧黄土,再到后面,黄土也不在了,只剩一片虚无。
何为虚无?便是一无所了。
我们生时,世界上多了一个“微不足道”的人;我们死时,世界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去有任何改变。从开始到结束,竟然是从零到零的一个过程。
仿佛,我们在世事间沉浮挣扎拼命追逐的一切仅仅是一场徒劳。想到此处,是何种感受呢?就是“怀疑”,怀疑这样的人生的意义何在。也许有人会说:“我有自己的孩子。我还留下了各种动产以及不动产。这些都可以证明我这一生多么的硕果累累,也都可以证明我存在过,证明我奋斗过。这便是意义。怎会是一场徒劳?”可是,孩子是永恒的吗?房子能耸立多久呢?孩子也会迎来“百年之后”,孩子的孩子也将迎来“生命的终点”……代代如此。
纵观历史,预演未来,再耐久的建筑,例如如今已经延续千百年的金字塔,也只不过今天还存在而已,更遑论,我们的房子也就是几十年的产权。如此来论,关于我们存在的证明也必将在时间长河里不断地被冲蚀,最后消失殆尽。
于是,有人说:“那我就创造出来一个比‘孩子以及房子’更长久存在的事物来。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?历史上,不是有很多成功案例吗?两千多前的孔子,苏格拉底等等,他们的肉体生命早已在两千多年前结束,化为无有,可是并不妨碍两千多年后的我们知道他们“存在过”。
甚至,可以预想,孔子,苏格拉底等人的‘存在事实’将会继续延申。圭璧在前,我们也可以如他们一样,穷己所有,创造出来一个精神的纪念碑或者‘孩子’,在我们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,继续在世间发光发热。这哪里是什么‘一无所有’呢?”这样说来,好像很有道理。思想,文化等等生命总是绵长的,如果够幸运,我们创造出来的是一个经典,看起来确实将会“永远”存在。
那么,问题又来了,孔子、苏格拉底等人在哪里看似不竭地存活着呢?在人类文明里,在我们身处或者可以预知的时空界限里。也就是,他们的存在长度又依托在所在的大土壤里——人类文明。
可是,从我们目前所知的物理学知识来看,或多或少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:宇宙起源于一个无质量无体积的奇点,从诞生的那一刻起,也在走向坍缩的结局。
那么,人类所在的世界,以及其所存在的宇宙也有一个有限度的“寿命”。这个寿命只是远远长于人的寿命但并不是没有尽头。
那么,到了人类或者宇宙寂灭的那一刻,所有现在看似永恒的“孔子、苏格拉底等”,也就随着一起化为无有。
这样说来,无论在肉体生命上,还是在精神生命上,都没有一个永恒。所有出现的,最终都会离开并不剩一物。
那么,此刻再来想,人生有何意义呢?
也许有人说,是有一个宏大的存在创造了这个世界。我们也因着这一创造本身就有了意义。比如上帝,比如盘古女娲等等。那么,它们又基于什么标准创造了这个世界?它做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?
在我们看来,创造是一种美好,可是或触目所及或充耳所闻,这场创造并不如我们所期待那样全是美好。要不然,也不会有那么多无奈的感叹,悔恨,痛苦等等。从各种角度,我们都无法判定这场创造有什么意义。
那么,如果这场创造毫无意义,身处其中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?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吗?如果整体都没有意义,“作为一部分”又有什么意义呢?
如此想来,似乎就得出了一个结果:人生没有意义。
但是,问题又来了。我们又是从何标准来评判“人生是否有意义呢?”,从前面所述来看,这一判定标准是死后所存以及其存在的时间长久——有事物留下并且此物永恒存在——如此,人生就是有意义。相反,就是没有意义。
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导向的视角:从结果来判定人生意义有无——有东西长久的留下就是有意义?没有东西留下就是无意义?是这样吗?
那么,过程论者是否同意这一判定呢?如果我们聚焦于人生中每一个正在发生,尚未产生结果的“当下”来评判“人生的意义”。
那么,又该如何来制定“有意义”的标准呢?假定,无论是日常琐事,还是人生大事,我们都在当下的概念来决定它的意义性,不去用一个结果来判定意义性。
如此以来,我们此刻做一个决定,做一件事情等等,“做”本身就有它意义。可是,当我们谈“有意义”的时候,就已经假定了一组概念——“有意义”和“无意义”。当下所“做”并非因为“做”这个动作发生了就自然具有意义,或者自然无意义,它仍旧需要一个判定。
那么,它的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?此时此刻的由内而外的感受——比如愉悦感等,然后呢?我们一切人生行为或者事件都可以用“当下的愉悦感等”来判定,很显然与前面的说法就产生矛盾了。
因为,“当下的愉悦感”本身也是一种结果导向视角。这就又回到了:人生的意义在于它的结果是否有意义。可如前所述,从结果导向来论,人生从一片虚空而来,又最终回到一片虚无,显而易见是无意义的。仿佛讨论到这有了一个结果——人生没有意义。可是,我们能满足这样的答案吗?如果,无论从短暂的肉体本身,还是从宏大的看不到尽头的宇宙叙事,我们的人生都没有意义。那么,这一切的开始和结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?
想到此处,写到此处,我的内心是一片迷思。“没有意义的人生”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呢?如果,这样活着,那样经过,最终并没有差别。我们该如何去“直视”每时每刻,直视最终“从零到零”的事实呢?这个世界仍旧有很多人,在知晓或者相信这一“事实”的情况下,仍在孜孜以求的追寻,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?是什么召唤着他们在这一片虚无中一往无前,以“虚无”为目的进行此刻的创造?
从前所论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,从目前可以想到的最宏大的视角来看,每个人的最终归处是一致的,但是,奇妙就在于,这个结果并不绝对决定甚至干预过程。我们仍旧在选择经过这一切以及抵达终点的独属于自己的方式。
对于每一个独特的人生,这一“可选择”是否就是意义所在?或者,对于整个人类,在“虚无”结局之下,去努力赋予意义就是意义所在呢?
谌洪果:
人生的意义不以世界的有无为前提
你写的《人生的意义》的读书札记很好,能够把作者的论证和观点“化用”为自己的表述和例证,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问题意识,然后尝试寻求答案,读起来很顺畅,还能引人进一步思考。我也从你的文字中受益。
你发现人们在谈论人生意义时,往往是“以结果为导向的视角”,这是恰当的概括。而且在分析问题时,先找到一个概念或命题切入,这样整个文章就有主心骨了,各种材料也能根据统一的范畴和思路组织起来。
以结果为导向意味着,人生的意义要根据是否有某种结果来衡量。问题在于,所有结果都是靠不住的,终究会消灭。如果结果本身是虚无的,人生的意义何在?很多人退而求其次说,既然无法期待结果,那我们就珍惜当下,在当下创造意义。你敏锐地看到,当我们在当下决定做或不做某事时,我们内心一定也有一个有没有意义的标准,比如做这件事能带来愉悦,能让自己充实,但愉悦和充实,仍然是结果为导向的,所以抓住当下的说法,也无法实现人生意义。
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,“以结果为导向”的概括,从社会科学分析范式的角度,是不错的,但这一提炼似乎还不够抽象,也就是不够哲学。更彻底一些,可以说,有关人生意义的分析,终究是以“有无”为导向的。这也是内格尔一以贯之的思路。
如果人生所依托的更大的东西是“有”,那就说明人生有意义;如果人生所依托的更大的东西终归于无,那就说明人生无意义。事实上,不管是时间维度,还是空间维度,更大的东西都是虚无,所以结论只能是人生是无意义的。
时间上,人类所创造的、所拥有的一切,从物质性产品到精神性产品,都会消失,无法永存;空间上,人类所依附的共同体或整体,无论是家庭、国家还是世界本身,也都会无限扩展下去,虚无之外是更大的虚无。
至于当下,以“有无”标准衡量,更是虚无。在时间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者当中,“现在”才是最不可能存在的,在你进入现在的那一瞬间,现在要么已经过去了,要么还没有到来。现在压根就没有存在过,所以什么珍惜当下都是空谈,无意义的。
你问了一个好问题:既然怎么论证人生都没有意义,为什么人们还是能够在虚无中一往无前,倾情投入呢?看来我们都有些不甘心,也许,我们仍然在选择抵达虚无的唯独属于自己的方式,这种独特性的方式本身,大概是有些意义的。最后你说,难道在虚无结局下,去努力赋予意义就是意义?
这样的结论也算是自圆其说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,聊以自慰了。但是,恐怕无法真正说服自己。所以你最后用的是问号。理由很简单,当我们直接面对彻底的虚无,我们根本就没有动力和能力去赋予什么生命的意义。那种在无意义中创造意义的说法,多半是自欺欺人。
你是学心理学的,应该知道一个密闭空间的心理实验,一个人在一个完全密闭的、静音的、无法接受任何外界刺激的空间里,是待不了几天就会崩溃的。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密闭空间,相对于完全的虚无,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
事实上,就连作者在最终结论也是:“也许生命不仅没有意义,而且也是一出荒诞剧?”对于生命的意义,作者也陷入了迷茫,而以问号结束。
现在,我也试着回答人生有没有意义的问题。我先说说我的感受。在阅读内格尔和你的关于人生意义的文字,以及在我与你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流的过程中,我觉得这样的讨论虽然没有答案,但确实是有意思的,至少比我用这段时间刷抖音有意思多了,因而也有意义多了。
你或许会立刻反驳说:既然怎么做都是虚无,那么做啥不都是一样的吗?怎么还会有一个意义高下的问题呢?
对此我要反其道而论之。
毫无疑问,对于做这件事比做那件事有意义,这是我真实的感受,是无法否认的。正因为人们就当下该做某事总会有意无意地有所比较和权衡,所以可能证明“虚无论”并不是绝对的。我们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做某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,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觉得某件事比另一件事更有意义。如果事情之间能够进行这种意义高下的比较(不管比较的标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),就表明并没有绝对的虚无,因为总得“有”某个据以比较的标准啊。
对于超越我们经验的之外、之上、之后的事情,到底是有还是无,我们是不知道的,毕竟人是有限的,有限无法真正理解无限。这就是不可知论。
因此,断然以“无”为前提讨论人生的无意义,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换言之,讨论人生的意义,没有必要纠结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最终是有还是无。人生的意义只能以人生为前提。人生之外,到底是有还是无,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这种有或无与我的人生是不是相关。
就像加缪所说:
“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断去死的。伽利略掌握着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,但一旦这个真理使他遭遇生命危险,他便轻而易举地弃绝生命……他的真理连火刑柴堆的价值都不如。到底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,压根儿无关大局。说穿了,这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。反之,我倒目睹许多人,因为觉得生活不值得过而轻生了事。我也看到有些人,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给了他们生的依据而为之献身。基于此,我断定生命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。”
这是加缪对生命意义的肯定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有(比如活着)还是无(比如死亡)支撑着人生的意义,而是在于,我们基于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断定,才去主动选择是有(活着)还是(无)。有或无这样的结果仅仅是结果而已,有无并不能作为意义的前提。意义就是自身的行动性,意义因而是个体性的,是我所看重的。意义是一种存在感,一种重要感。
说到底,我们存在,所以我们关心自己的存在,而就我的确存在这一点儿言(哪怕我此刻在梦中,我在梦中也是存在的),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寻求自己人生的意义。这可以称为“人生意义的内在性”。不必要悲情地在虚无中创造本不存在的意义,而是要在本就存在的意义中开掘生命的实在性和主体性。意义不取决于我们拥有的东西,我们所做的事情,意义就是我们之所以拥有、之所以去做以及之所以为之欢笑为之哭泣的东西。
那种“人生无意义”的说法是大而化之的。意义永远都是在的,但意义的确可能被耗费。人生之所以无意义,还是因为人自己把它整得无意义了。
一个人真要贯彻人生毫无意义的原则,那他就连“人生无意义”这句话也不该说出口。但既然他已经说了“人生无意义”,就证明他想要说服人们或自己相信人生是无意义的。
就他试图说服这件事而言,对他还是有点意义的。
注册会员查看全部内容……
限时特惠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年会员只要98元,全站资源免费下载
点击查看详情
站长微信:9200327